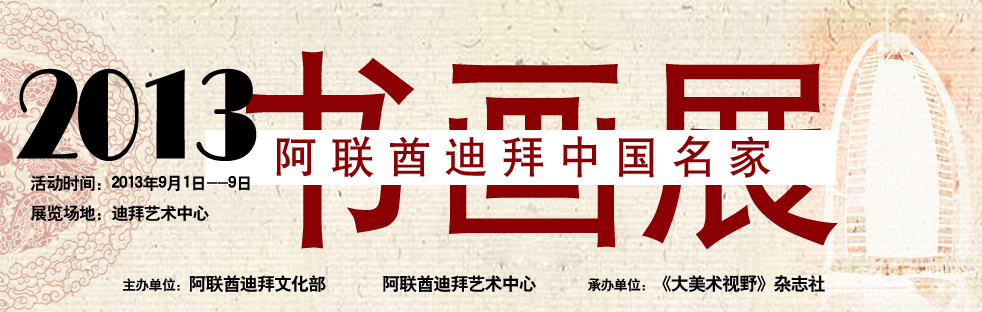陈亚凡:漆画的解读与践行--程向君访谈录(4)
三、推陈出新 践行自我漆画艺术风格
陈:您漆画创作转向抽象风格之后,除了表现手法的独特,观者解读您作品最大的兴趣点莫过于作品中存有大量的文化符号。中医的手印、藏传佛教的经文、书画中的印章,这些文化符号原本属于各类“已有”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属于一种“公共”的图像,将这些“公共”的、“已有”的图像融入到您个人作品中,并构成了画面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进而形成个人独特的艺术表征,必然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您是如何来把握、完成这种转化的?
程:这是对传统文化从吸收、提炼到表现的一个过程,首先要说的就是画外的功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遗存一直存有浓厚的兴趣,自己也喜欢收藏,还有住在北京四合院的生活体验,都是我汲取传统文化资源的途径。一个建筑构件的肌理、一个墙体的结构、一个陶器的质感……在这些微观的视觉经验中我捕捉到了历史沉积的厚重感,而从那些历史流传下来的图像与文字中我看到了中华文明延续的一种脉象,它们与我的兴趣点相重合。以何种方式来表达,实际上涉及到了对内心感受的把握和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两个方面,需要提炼和升华。对传统文化脉搏的提炼以及超越表面物象的一种升华,最终反映到画面中就是对文化符号的选取与运用方式。
在我看来,这些图像或文字之所以被称为文化符号,是因为它们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背景信息,是可以被解读、被揣测的,当它们作为一种视觉形象进入画面构架之中,其文化背景信息也随之进入,二维平面的图式就有了历史空间向度的延展。这时,文化符号就已超越了一般性的叙事,而承担了我主观所要表达的某种精神内涵的象征功用。换句话说,我对传统文化重新解读与构架,反映在对这些文化符号的运用过程中,反映在我处理图像、材料、表现形式三者的关系中,包括如何利用材料、技术使文化符号成为我作品中点线面的构成要素,这样,文化符号就已经从一种“已有”的、“公共”的,转化为“重构”的、“个人”的。并且,“重构”以“已有”为支撑,“个人”以“公共”为基础,“重构”就不是空穴来风,“个人”也就不是孤立无援的。
陈:医书系列和藏域文化系列是您转向抽象风格之后两大重要创作内容,请您具体谈一谈其中文化符号的选用以及表现方式。
程:在医书系列作品中,我所选取的手印、面相等图像,背后隐含着中国人对个体生命、个体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方式,但对于当代人而言,这些图像却如同天书一样,时间上的距离演化为文化上的间断,这是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疏离和陌生。我采用平面的处理方法,并有意识地分出了不同的材料层,保留了不同时间完成的作业面,表现手法上吸取了中国民间木板年画的形式,也受到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启示,硬边的框架、流动的笔触,再加上褐色漆液罩染,突出了一种神秘的东方气韵,是对“似曾相识”图像的生疏所引发的独特触动,表达了当代人对于传统文化一种既“亲密”又“游离”的状态。
藏域文化系列的创作与我多次去西北藏区考察写生的经历有关,那里的地域风貌、风俗特质,以及藏族人对自然的膜拜和对宗教信仰的虔诚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将藏域佛教中常见的印经板作为它的文化符号提取出来,与画面的构成、漆材的特质结合在一起——在堆厚的漆灰上面印压出经文或是图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仿制样式的过程,而是对藏域文化认知与体悟后的表达过程,画面也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视觉效果。
陈:您近期的作品相较医书系列、藏域文化系列而言,构成上更加洗练,色彩上也更加单纯,是不是表明一种新的探索方向正在您的创作中形成?
程:我的创作始终都处在一个自我更替的过程中。最近我在看吴冠中先生写的随笔,吴先生很重视“求新”,这是他艺术追求一个核心,我想这也是每个艺术家都应追求的,创作始终要保持一种鲜活力。我进入抽象风格创作后,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演进过程,才会由最初的“繁”走到今天的“简”,这些年所创作的每一幅作品,都记录着我对传统文化认识和把握的过程。现在,我想通过更加洗练的块面、更加单纯的材料来表现一种强烈的视觉图式,以此传达出一种东方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背后的隐语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回归,也正是有了这种自信,我才敢于选择最简练的方式去表达。
陈:在这批作品中,文化符号的使用似乎更加含蓄,具体汉字图像已经很少直接地出现在画面中,观者只能在巨大的黑色块面中隐约感到某个汉字偏旁部首结构的存在。
程:的确,我是从汉字的偏旁部首以及中国书法的书写中得到了重要的启示。我一直很喜欢也很关注中国的书法,从甲骨文到真草隶篆,书法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和美学思想,本身的造型样式也具有高度的抽象形式。创作中,我将具体的字义完全抽离出去,把它演绎成一个偏旁结构或是纯抽象的构成形式,然后将其无限地放大,再经过笔触的叠加,使画面的视觉效果变得更加强烈,我在其中寻找一种中国元素和绘画语言之间的和谐的结构关系。并且,书法的书写过程有很多即兴的成分,可以直接反映出人的心灵轨迹 ——当一笔顺势写下,其时的心灵感受均可反射出来,这也是我所追求的艺术表达状态。虽然用漆材料来做书写,不像使用水墨那么潇洒,但是漆自有它的特点——可塑性强、可以堆高,比起水墨它更具有视觉冲击力,所释放出来的气息也更为强烈。
另外,在这一批作品中我都采用一个印章——我自己的名章,作为画面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明清绘画里面都有很多收藏名章,其中里面最突出的就是太上皇之印,尽管这不是原作品中的一部分,是后来收藏者的行为——表示一种所有权,也代表着一种身份地位,但它往往占据在画面重要的位置,很霸气,以至于今天我们去赏析这些传世之作时,那些收藏之印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绘画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我在作品的书法构成之中使用印章形式,首先二者的关系是和谐统一的。同时,这个名章既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符号,符号指向的交错与重合,使它又有了多层次的解读空间。在制作中,我用稠厚的漆泥在漆板上打章,有着行动绘画的感觉——漆泥在流动,像被抓起来一样,让我也逐渐意识到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其结果就是让这种感觉变成一种坚信——这就是你的艺术风格!
陈:您漆画创作转向抽象风格之后,除了表现手法的独特,观者解读您作品最大的兴趣点莫过于作品中存有大量的文化符号。中医的手印、藏传佛教的经文、书画中的印章,这些文化符号原本属于各类“已有”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属于一种“公共”的图像,将这些“公共”的、“已有”的图像融入到您个人作品中,并构成了画面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进而形成个人独特的艺术表征,必然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您是如何来把握、完成这种转化的?
程:这是对传统文化从吸收、提炼到表现的一个过程,首先要说的就是画外的功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遗存一直存有浓厚的兴趣,自己也喜欢收藏,还有住在北京四合院的生活体验,都是我汲取传统文化资源的途径。一个建筑构件的肌理、一个墙体的结构、一个陶器的质感……在这些微观的视觉经验中我捕捉到了历史沉积的厚重感,而从那些历史流传下来的图像与文字中我看到了中华文明延续的一种脉象,它们与我的兴趣点相重合。以何种方式来表达,实际上涉及到了对内心感受的把握和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两个方面,需要提炼和升华。对传统文化脉搏的提炼以及超越表面物象的一种升华,最终反映到画面中就是对文化符号的选取与运用方式。
在我看来,这些图像或文字之所以被称为文化符号,是因为它们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背景信息,是可以被解读、被揣测的,当它们作为一种视觉形象进入画面构架之中,其文化背景信息也随之进入,二维平面的图式就有了历史空间向度的延展。这时,文化符号就已超越了一般性的叙事,而承担了我主观所要表达的某种精神内涵的象征功用。换句话说,我对传统文化重新解读与构架,反映在对这些文化符号的运用过程中,反映在我处理图像、材料、表现形式三者的关系中,包括如何利用材料、技术使文化符号成为我作品中点线面的构成要素,这样,文化符号就已经从一种“已有”的、“公共”的,转化为“重构”的、“个人”的。并且,“重构”以“已有”为支撑,“个人”以“公共”为基础,“重构”就不是空穴来风,“个人”也就不是孤立无援的。
陈:医书系列和藏域文化系列是您转向抽象风格之后两大重要创作内容,请您具体谈一谈其中文化符号的选用以及表现方式。
程:在医书系列作品中,我所选取的手印、面相等图像,背后隐含着中国人对个体生命、个体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方式,但对于当代人而言,这些图像却如同天书一样,时间上的距离演化为文化上的间断,这是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疏离和陌生。我采用平面的处理方法,并有意识地分出了不同的材料层,保留了不同时间完成的作业面,表现手法上吸取了中国民间木板年画的形式,也受到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启示,硬边的框架、流动的笔触,再加上褐色漆液罩染,突出了一种神秘的东方气韵,是对“似曾相识”图像的生疏所引发的独特触动,表达了当代人对于传统文化一种既“亲密”又“游离”的状态。
藏域文化系列的创作与我多次去西北藏区考察写生的经历有关,那里的地域风貌、风俗特质,以及藏族人对自然的膜拜和对宗教信仰的虔诚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将藏域佛教中常见的印经板作为它的文化符号提取出来,与画面的构成、漆材的特质结合在一起——在堆厚的漆灰上面印压出经文或是图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仿制样式的过程,而是对藏域文化认知与体悟后的表达过程,画面也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视觉效果。
陈:您近期的作品相较医书系列、藏域文化系列而言,构成上更加洗练,色彩上也更加单纯,是不是表明一种新的探索方向正在您的创作中形成?
程:我的创作始终都处在一个自我更替的过程中。最近我在看吴冠中先生写的随笔,吴先生很重视“求新”,这是他艺术追求一个核心,我想这也是每个艺术家都应追求的,创作始终要保持一种鲜活力。我进入抽象风格创作后,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演进过程,才会由最初的“繁”走到今天的“简”,这些年所创作的每一幅作品,都记录着我对传统文化认识和把握的过程。现在,我想通过更加洗练的块面、更加单纯的材料来表现一种强烈的视觉图式,以此传达出一种东方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背后的隐语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回归,也正是有了这种自信,我才敢于选择最简练的方式去表达。
陈:在这批作品中,文化符号的使用似乎更加含蓄,具体汉字图像已经很少直接地出现在画面中,观者只能在巨大的黑色块面中隐约感到某个汉字偏旁部首结构的存在。
程:的确,我是从汉字的偏旁部首以及中国书法的书写中得到了重要的启示。我一直很喜欢也很关注中国的书法,从甲骨文到真草隶篆,书法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和美学思想,本身的造型样式也具有高度的抽象形式。创作中,我将具体的字义完全抽离出去,把它演绎成一个偏旁结构或是纯抽象的构成形式,然后将其无限地放大,再经过笔触的叠加,使画面的视觉效果变得更加强烈,我在其中寻找一种中国元素和绘画语言之间的和谐的结构关系。并且,书法的书写过程有很多即兴的成分,可以直接反映出人的心灵轨迹 ——当一笔顺势写下,其时的心灵感受均可反射出来,这也是我所追求的艺术表达状态。虽然用漆材料来做书写,不像使用水墨那么潇洒,但是漆自有它的特点——可塑性强、可以堆高,比起水墨它更具有视觉冲击力,所释放出来的气息也更为强烈。
另外,在这一批作品中我都采用一个印章——我自己的名章,作为画面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明清绘画里面都有很多收藏名章,其中里面最突出的就是太上皇之印,尽管这不是原作品中的一部分,是后来收藏者的行为——表示一种所有权,也代表着一种身份地位,但它往往占据在画面重要的位置,很霸气,以至于今天我们去赏析这些传世之作时,那些收藏之印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绘画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我在作品的书法构成之中使用印章形式,首先二者的关系是和谐统一的。同时,这个名章既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符号,符号指向的交错与重合,使它又有了多层次的解读空间。在制作中,我用稠厚的漆泥在漆板上打章,有着行动绘画的感觉——漆泥在流动,像被抓起来一样,让我也逐渐意识到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其结果就是让这种感觉变成一种坚信——这就是你的艺术风格!
(责任编辑:王 理)
文章热词: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美术圈的立场,也不代表美术圈的价值判断。
延伸阅读: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