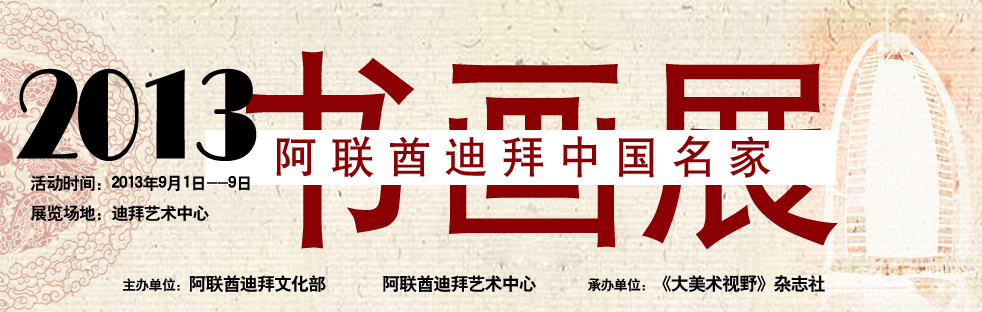陈亚凡:漆画的解读与践行--程向君访谈录(2)
陈:1996年,您作为《中国美术全集•漆画卷》的副主编,在该书卷首发表了《中国漆画40年》一文,不但对全国漆画创作状态做了详实的概述,更明确地提出了“漆画之本,在于艺术”的观点。这一观点的表明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漆画的艺术评判标准问题。而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多关于漆画的文章所讨论的热点均集中在“天然漆与化学漆之争”方面。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超越“材料之争”的“时代热点”问题,较早地进入对漆画艺术本质的思考?
程:这主要得益于编辑《中国美术全集•漆画卷》的过程,它使我有机会全面考察了当时漆画创作的整体状态及作品风貌。考察带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中国南北地域跨度那么大,漆画作品间的差异却仅体现在漆材料的选用方面——福建天然漆、江西化学漆、广东江阳漆以及北京的混合漆材,而作品本身却大同小异——创作内容无外乎民居、静物、少数民族人物几类,创作风格更是呈现出整齐划一的唯美装饰风格。这说明当时的漆画创作与整体画坛已处于一种脱离状态。“八五新潮”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各种新画风孕育形成,而漆画作者依然固步自封于传统漆工艺之中,关注点囿于材料与工艺层面,很少涉及到艺术上的讨论。这对一个画种的长远发展,无疑是不利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认为,要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关键在于漆画作者观念的转变,只有在观念上修正原有的评判标准,才能将漆画创作从“唯材料论”“唯技艺论”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才能引导漆画作者回到对绘画本质的探讨之中。
陈:我注意到您的个人创作,正是在您提出“漆画之本,在于艺术”这一观点之时,发生了明显的转型,作品风格由具象转向抽象,表现手法开始采用“厚涂”的方法。
程:是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是我学习传统漆工艺、初步探索漆画表现的阶段。1986年我从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留在刚刚成立的漆画工作室,从事教学工作。教学的需要,加上个人创作的需要,我觉得有必要对传统漆工艺作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80年代末我多次下厂学习传统漆工艺,包括到山西新绛的漆工厂学习刻漆、刻灰等技艺。同时,也吸取了中央工艺美院一些好的传统,包括乔十光先生漆画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意境以及装饰风格。那一阶段我将唯美装饰风格的进一步深化,作为自己的主要创作方向。创作内容多选择我熟悉的景物,有身边的静物,也有外出写生所见的风景。虽然取得了一些创作成果,90年代前期举办了几次个人漆画展,并有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但是,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慢慢地我发现,单一的装饰风格与我个人的审美理想并不吻合。
我开始思考如何突破漆画的既有模式,并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比如,1995年我创作了《垂死的鱼》这幅作品,出发点就是要深度挖掘漆材的写实表现力。这之前,漆画一直被认为不适合表现写实题材。我想检验一下,漆画表现写实题材到底有没有可能,它是否能传达出古典绘画的审美气息。在具体创作中,我利用交叉形的构图、恣意豪放的笔触,以及“薄料”与棕黑色漆液所形成的色彩对比关系,营造出一种古典绘画的审美气息。同时还创作了《鸡冠花》《母女》等,可以说最终的作品达到了我预求的效果,也验证了漆材料除传统漆工艺髹饰表现体系之外,在绘画领域中还存有很大的表现空间。
到1996年,经过考察和反思,我对漆画创作的认识变得更加清晰。对于一个漆画家来说,学习和继承传统漆工艺是重要和必要的,但学习和继承的目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重复前人的样式,而是在汲取传统漆工艺的养分之后,有目的地择取适合作品精神传达的表现手法才是关键,唯有如此,技艺才能真正成为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媒介。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才能从单一的唯美装饰风格中走出来,转向个性化的抽象风格;才敢于突破传统漆工艺的表现样式,将原来漆画制作过程中的一部分笔触、痕迹不经打磨地保留下来,使其成为作品的一部分。
陈:从表面样式来看您转型后的漆画作品,除了表现手法有极大的突破之外,在漆画底板的选用方面也更加宽泛。传统漆画一般都是在封漆的木板上进行制作,而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创作了许多箔上漆画与布上漆画,近年又创作了大量的纸上漆画,不拘一格的创作方式同样给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受。
程:做板封漆的目的只有一个,防止漆画底板变形。以水打磨是漆画制作中常用的方法,为了避免水浸入底板而发生变形,双包制板、裱布刮灰、多次刷漆就成了必备的工序。但如果在漆画制作过程中,减少打磨工序或者采用局部水磨的方法,只要操作得当,同样可以避免底板走形,当然这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只要能保证底板相对平整,不影响漆画创作,做板封漆就不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漆画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需要选择不同材质的底板。底板不同,其特质就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板材坚实沉厚;箔材属于软金属材料,具有较强的反射力和可塑性;苎麻质地挺括且纹理疏朗;卡纸表面光滑、色泽洁白……实际上,从选择底板开始,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和审美表达就已经蕴含其中了。
在近期大量的纸上漆画创作过程中,我体验到了一种即兴的、实验性的放松与愉快。这种放松和愉快并不是因为我创造出来了某种样式,而是我体会到了一种绘画的快乐。随着手中画笔的挥洒,漆液顺畅地在光洁的白卡纸上铺延、叠撞、流淌、浸染,笔笔舒展,处处生意,自然而又自得,直接而又直观。直抒心中意趣的快乐,这是在传统漆画制作模式中很难找到的一种情绪。
假如一种材料或技术不适合画家很随意地使用和掌控的话,反而容易导致对材料或技术本身的过分关注,舍本求末的最终结果,将会阻碍到绘画本身的发展。漆画作为工艺材料特征较强的绘画,创作者应处理好工艺与画面之间的关系,将技艺“隐藏”在画面的背后,从绘画视觉语言层面做好漆画文章。
程:这主要得益于编辑《中国美术全集•漆画卷》的过程,它使我有机会全面考察了当时漆画创作的整体状态及作品风貌。考察带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中国南北地域跨度那么大,漆画作品间的差异却仅体现在漆材料的选用方面——福建天然漆、江西化学漆、广东江阳漆以及北京的混合漆材,而作品本身却大同小异——创作内容无外乎民居、静物、少数民族人物几类,创作风格更是呈现出整齐划一的唯美装饰风格。这说明当时的漆画创作与整体画坛已处于一种脱离状态。“八五新潮”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各种新画风孕育形成,而漆画作者依然固步自封于传统漆工艺之中,关注点囿于材料与工艺层面,很少涉及到艺术上的讨论。这对一个画种的长远发展,无疑是不利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认为,要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关键在于漆画作者观念的转变,只有在观念上修正原有的评判标准,才能将漆画创作从“唯材料论”“唯技艺论”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才能引导漆画作者回到对绘画本质的探讨之中。
陈:我注意到您的个人创作,正是在您提出“漆画之本,在于艺术”这一观点之时,发生了明显的转型,作品风格由具象转向抽象,表现手法开始采用“厚涂”的方法。
程:是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是我学习传统漆工艺、初步探索漆画表现的阶段。1986年我从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留在刚刚成立的漆画工作室,从事教学工作。教学的需要,加上个人创作的需要,我觉得有必要对传统漆工艺作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80年代末我多次下厂学习传统漆工艺,包括到山西新绛的漆工厂学习刻漆、刻灰等技艺。同时,也吸取了中央工艺美院一些好的传统,包括乔十光先生漆画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意境以及装饰风格。那一阶段我将唯美装饰风格的进一步深化,作为自己的主要创作方向。创作内容多选择我熟悉的景物,有身边的静物,也有外出写生所见的风景。虽然取得了一些创作成果,90年代前期举办了几次个人漆画展,并有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但是,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慢慢地我发现,单一的装饰风格与我个人的审美理想并不吻合。
我开始思考如何突破漆画的既有模式,并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比如,1995年我创作了《垂死的鱼》这幅作品,出发点就是要深度挖掘漆材的写实表现力。这之前,漆画一直被认为不适合表现写实题材。我想检验一下,漆画表现写实题材到底有没有可能,它是否能传达出古典绘画的审美气息。在具体创作中,我利用交叉形的构图、恣意豪放的笔触,以及“薄料”与棕黑色漆液所形成的色彩对比关系,营造出一种古典绘画的审美气息。同时还创作了《鸡冠花》《母女》等,可以说最终的作品达到了我预求的效果,也验证了漆材料除传统漆工艺髹饰表现体系之外,在绘画领域中还存有很大的表现空间。
到1996年,经过考察和反思,我对漆画创作的认识变得更加清晰。对于一个漆画家来说,学习和继承传统漆工艺是重要和必要的,但学习和继承的目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重复前人的样式,而是在汲取传统漆工艺的养分之后,有目的地择取适合作品精神传达的表现手法才是关键,唯有如此,技艺才能真正成为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媒介。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才能从单一的唯美装饰风格中走出来,转向个性化的抽象风格;才敢于突破传统漆工艺的表现样式,将原来漆画制作过程中的一部分笔触、痕迹不经打磨地保留下来,使其成为作品的一部分。
陈:从表面样式来看您转型后的漆画作品,除了表现手法有极大的突破之外,在漆画底板的选用方面也更加宽泛。传统漆画一般都是在封漆的木板上进行制作,而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创作了许多箔上漆画与布上漆画,近年又创作了大量的纸上漆画,不拘一格的创作方式同样给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受。
程:做板封漆的目的只有一个,防止漆画底板变形。以水打磨是漆画制作中常用的方法,为了避免水浸入底板而发生变形,双包制板、裱布刮灰、多次刷漆就成了必备的工序。但如果在漆画制作过程中,减少打磨工序或者采用局部水磨的方法,只要操作得当,同样可以避免底板走形,当然这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只要能保证底板相对平整,不影响漆画创作,做板封漆就不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漆画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需要选择不同材质的底板。底板不同,其特质就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板材坚实沉厚;箔材属于软金属材料,具有较强的反射力和可塑性;苎麻质地挺括且纹理疏朗;卡纸表面光滑、色泽洁白……实际上,从选择底板开始,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和审美表达就已经蕴含其中了。
在近期大量的纸上漆画创作过程中,我体验到了一种即兴的、实验性的放松与愉快。这种放松和愉快并不是因为我创造出来了某种样式,而是我体会到了一种绘画的快乐。随着手中画笔的挥洒,漆液顺畅地在光洁的白卡纸上铺延、叠撞、流淌、浸染,笔笔舒展,处处生意,自然而又自得,直接而又直观。直抒心中意趣的快乐,这是在传统漆画制作模式中很难找到的一种情绪。
假如一种材料或技术不适合画家很随意地使用和掌控的话,反而容易导致对材料或技术本身的过分关注,舍本求末的最终结果,将会阻碍到绘画本身的发展。漆画作为工艺材料特征较强的绘画,创作者应处理好工艺与画面之间的关系,将技艺“隐藏”在画面的背后,从绘画视觉语言层面做好漆画文章。
(责任编辑:王 理)
文章热词: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美术圈的立场,也不代表美术圈的价值判断。
延伸阅读:
网友评论